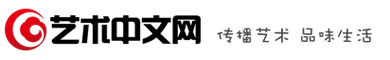|
|
盜火計劃:翟春陽個展
盜火計劃:翟春陽個展 Stealing Fire: Zhai Chunyang’s Solo Exhibition 藝術家:翟春陽 策展人:郭赟 出品人:黃嘯 展覽總監:蔡立樂 展覽統籌:劉鑫 策展助理:李思婷 展覽時間: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31日 開幕時間:2024年12月21日15:30 展覽地點:美侖美術館·圣之空間 展覽地址:朝陽區酒仙橋2號798中二街D09 主辦:美侖美術館·圣之空間 協辦:湖廣(深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支持:湖南省油畫學會 Artist: Zhai Chunyang Curator: Guo Yun Producer: Huang Xiao Director: Cai Lile Coordinator: Liu Xin Curatorial Assistant: Emma Lee Exhibition Period: December 20, 2024 - December 31, 2024 Opening: 3:30 PM, December 21, 2024 Venue: Meilun Art Museum - SZ Art Center Address: D09, 798 Art Zone, No.2 Jiuxian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Organizer: Meilun Art Museum - SZ Art Center Co-organizer: HUKAMA Supporting Unit: Hunan Oil Painting Society “盜火者”翟春陽 文|郭赟 翟春陽身材瘦削,目光深邃,因不修邊幅而帶著點兒湘西匪氣,但言談間又夾雜著幾分書生氣的儒雅。他慣于沉默和安靜,讓人誤以為性格溫馴,然而,他的作品顛覆了這種印象,翟春陽作品中充斥著慷慨激越的情感以及對幽暗玄冥的洞察讓人確信,他更像是一個刺客、一個藝術上的革命者、一個抗擊暗夜的“盜火者”!他的作品及其藝術實踐構建了一個完整而隱秘的“盜火計劃”。 啟蒙 時過境遷,湘西早已不再像印象中那般神秘而粗礪,但某些根藏于意識深處的東西留傳了下來。翟春陽八十年代初生于湘西懷化一個名為辰溪的小鎮,辰溪名字富于詩意,古稱辰陽,意為辰水之陽,陽光照耀的水岸,屬荊楚之地,連接楚、巫、黔等地,為全楚交通咽喉。大概是因為地理上通達四方,懷化人喜歡走出去闖蕩生活,這既為翟春陽日后的闖蕩求學埋下了伏筆,也植入了在藝術上游牧與逆反的骨子里的基因。 改革開放之初,三線1之外村鎮普遍貧困且落后,掃盲依然是社會和時代的重要課題,知識分子對很多人而言如同鏡花水月,遙遠、虛妄而不切實際。但畫畫這個事兒對于翟春陽來說似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原動力,在幼年時期就與眾不同,他自己也很早就察覺到了自己在這方面與眾不同的才能。誘發翟春陽走向藝術道路的契機來自小學的美術課。與今日小學里豐富的師資力量不同,八十年代的普遍現實是一個老師往往身兼多職教授多門課程,美術課作為一門并不重要的文娛課程由其他老師代理是常態。當時翟春陽的美術老師由語文老師兼任,而語文老師因為喜好文學,時常有意引導學生用文學典故激發藝術想象,這充分釋放了翟春陽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因此在美術課上大放異彩。老師也對他的畫作大加贊賞,甚至把小春陽的畫作公示全班以作褒獎。榮耀的光環讓翟春陽對自己繪畫上的才能無比自豪,由此一發不可收拾,不斷在繪畫的世界里自由馳騁翱翔。及至中考,因考市重點一中競爭激烈,基于升學壓力,老師建議直接學美術。當時懷化師專有專門教授美術課的美術班,學費不過幾十元而已。翟春陽懷著忐忑的心情向正在打麻將的老媽說了自己想報名美術班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平時很摳門的老媽忽然大方起來,直接給了翟春陽整整一百塊錢讓他去學美術。 師專的美術老師成為了翟春陽藝術道路上的啟蒙導師,他喜歡念叨梵高和印象派的故事,時常給學生講訴現代主義對古典傳統的背離、反叛與革命,并激勵學生奮發學習,鼓動他們向大師看齊。這為翟春陽的藝術道路指明了方向,既在潛意識里植入了對波西米亞式自由世界的向往,也暗示了作為藝術家為藝術殉道的宿命。
《朗誦者》,160×180cm,布面丙烯,2022 大學 對于翟春陽而言,考上美院并不意外。 多少是出于擺脫小鎮上閑散的賭博風氣,也是出于對自己藝術上天賦和狂熱的自信,在經歷寒窗之后,考上美院出走他鄉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翟春陽很快發現大學并非理想照進現實,美院生活太閑適,太容易沉溺于某些被壓抑的欲念與惡習,這在同學中間并不鮮見,但對翟春陽而言既難以理解,也不可接受。與此同時,翟春陽考上的西安美術學院從來不是一個激進的學院,后文革時代藝術為工農兵服務的“黃土畫派”是當時的主流,與其熱情向往的印象派畫家在現代主義草創之初那些震驚世界的革命性壯舉以及狂放不羈的波西米亞式生活相去甚遠。翟春陽開始重新思考藝術的現代史,也反思自己所學是否已經趨于保守,基于此,沒多久便搬出了宿舍自己租房獨自畫畫。 即便當時房租每個月只要一百塊錢,對來自窮鄉僻壤的翟春陽而言依然是昂貴的,因此大學生活過得十分拮據。但翟春陽樂此不疲,每日沉浸在自己的藝術世界里,只要稍有余裕,便毫不吝惜地購買畫材,也因為并不寬裕,不得不省吃儉用換顏料,買顏料的時候也必須得精打細算,盡量多買損耗比較多的白色顏料。就這樣,翟春陽自立于學院之外,與弗洛伊德、尼采、福柯、海德格爾等為伴,同時也像印象派畫家那樣從身體和精神上自我放逐和流浪,苦修式地尋找自己想要的繪畫感覺。 畢業之后,翟春陽回到了家鄉的省會城市長沙,一邊工作一邊幾近偏執地繼續踐行自己的藝術理念。或許如陳丹青所言,眼界開了并不一定是好事,藝術家需要不斷深耕自己的世界,而克萊門特·格林伯格認為現代藝術的革命是由內而外的,二者不謀而合。
《天堂電影院》,140×140cm,布面油畫,2015 繪畫 繪畫作為一種藝術語言媒介,或許已經很難再有革命性巨變,這早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知,格林伯格在上個世紀中期就開始提醒“架上繪畫”的危機,認為繪畫正在淪為某種室內空間的平面圖案壁紙2,意指繪畫逐漸演變為庸俗文化的附庸。無獨有偶,阿瑟·丹托亦認為繪畫藝術正漸行失去動力和后勁,并進一步聲稱藝術走向了終結——但是丹托始終強調他僅指審美時代的終結,或者現代主義的終結,丹托更志于力證另一個藝術時代的開始:“‘藝術的死亡’可以解釋為美的藝術的死亡,這是一種政治宣言。這是一種革命性的吶喊,就像打倒統治階級!”3其實黑格爾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經明確指出了藝術某一個時代的終結,阿瑟·丹托、讓·鮑德里亞以及漢斯·貝爾廷均可視為后黑格爾時代藝術終結論者,但他們所指更多在于藝術時代的更迭,而這種更迭首當其沖便是繪畫。當然,多少也可以揣測他們出于藝術史的野心。作為一種技藝、語言或者媒介,繪畫藝術顯然不會走向消亡,依然是藝術實踐的重要方式,即便當代藝術的理念已經發生了巨變,繪畫藝術長久以來作為人類情感共振的載體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值得探討的是丹托所宣稱的“哲學綁架了藝術”的后歷史時代——即后現代之后的當代,繪畫將在藝術的新歷史時期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是在當代語境中討論未來繪畫形態的語言學意義或曰方法論意義,翟春陽的繪畫及其藝術歷程無疑是一個典型個案。 2020年,翟春陽在筆記里記述過自己當時的心境: “繪畫不止是反映災難,也不限于直接講述現實,繪畫的意義和目標遠大于此。繪畫是藝術家的精神自傳,我們無需語言,無需描述,只要去觀看,其中存有著更大的信息。” 無論是對環境的反映還是情感的表達,從技術進步的角度而言,影像、裝置、多媒體以及數字藝術等確實可以制造很多視覺上的刺激,但是繪畫作為根植于意識深處的符號化語言,就視覺或者心理上的共振而言更加直接、強烈且恒久!翟春陽的繪畫充滿了表現主義的情感張力,筆觸自由、迅捷而飽滿,色彩同樣充斥著飽滿的情感宣泄,但事實上翟春陽非常謹慎地使用大面積的灰度色系把一些歷史的或者個人的情緒非常直白地置于畫面之上,而非鮮艷奪目的色彩,通常僅僅使用沉寂的血紅或者冷灰色調,這營造了畫面的歷史感,是對某種特定情緒的強化,也具有一種素描的力量感。翟春陽的畫法摒棄了那種學院的嚴謹性和油滑的熟練性,從藝術家過往的經歷來看,當是有意識地保留了這種野性的語言,這使得畫面更加具有說服力。這種畫法從精神內核而言與一段時間以來藝術界流行的“壞畫”法有共通之處,都以粗礪解構精良,但是并不反繪畫。 繪畫并不意味著意識上的后退,只是對語言、媒介或者符號的選擇,其背后的價值意義取決于最終的繪畫以及背后的藝術家所承載的文化、哲學、時代、歷史、價值觀等等。繪畫語言本身即是力量,因此,翟春陽曾給自己某一場個展命名為“繪畫不死”。 當然,不僅僅是繪畫!
《黑夜》,30×20cm,布面丙烯,2024 盜火 翟春陽的繪畫中反復出現擎著火把的人,火把的光芒似乎在指引著某個方向,同時也照耀著無意識地聚集在一起的荒誕的人群。這是一個隱喻——為諸眾帶來光明與熱情的盜火者隱喻,這個隱喻并非普羅米修斯從太陽神那盜火種為人類獻祭般宏大,對翟春陽而言,這是一個反復出現在腦海中的形象,揮之不去因而信手涂繪,或許,這個盜火者的隱喻僅僅只是向內的。另一個關于火的隱喻或許更接近翟春陽的真實意圖,在柏拉圖的“洞穴之喻”4中,有一個有意思的推論:如果逃出洞穴的囚犯看到了真實的世界,他將如何說服那些把墻上的影子當作真實世界的囚犯放棄虛幻的執念?這個說服的過程意味著某種危險,因為他出走看到了真實的世界之后,看墻上的影子甚至不如一直呆在洞穴里的囚犯看得更清晰,他的說教很可能被當作某種愚蠢的行為,最后的結局很可能不是為洞穴里的囚犯指明出路,反而有可能被囚犯們孤立甚至群起而攻之。但是如果出逃者盜走了囚犯們身后的火把,或許囚犯們會意識到墻上的影子的虛無性并進而關注到自身存在及改變命運。翟春陽對繪畫藝術的堅持以及對藝術圈的疏離一方面意味著對傳統理念的悖離,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精神上的自我重建。翟春陽正是像一個逃出洞穴的藝術家,卻又試圖回到洞穴做一個繪畫藝術的盜火者,他在繪畫和藝術上的實踐組成了一個綿延的“盜火計劃”。 如果說“盜火”帶著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理想與對世界的樸素想象,那么在繪畫中如何實現且踐行自己的理念,并把現實、理想與想象熔入自己的整個藝術實踐中,鍛造一個個人化的烏托邦世界,這是藝術家波西米亞式的狂熱。火把、荊棘、領袖和諸眾反復出現在翟春陽的作品中,荒誕而現實的景觀雜糅著藝術史中的經典圖式片段,這些構成了翟春陽繪畫中充滿象征性和隱喻性的符號。在作品《歸》中騎著駿馬的骷髏舉著熊熊燃燒的火把穿越滿布荊棘的暗夜,高聳而未知的群山充滿未知的壓迫感,但是又伴隨著火光一起燃燒,作品帶著某種浪漫主義的想象,當然無疑更是現實世界的隱喻,正如堂吉訶德的歸來,命運是注定的,但身后的世界是不可知的。《天堂》則借用了米開朗琪羅在《創世紀》中上帝與亞當食指觸碰的瞬間,在《創世紀》中,上帝從天而降伸出右手食指,向神情茫然的亞當伸出的左手食指注入神明的靈魂,而在翟春陽的作品中,高臺上幾欲退縮的盜火者舉著火把似乎在阻斷亞當與上帝的觸碰,而臺下瞠目而視的諸眾緊張地看著這驚險的瞬間。這是一個歷史和現實的隱喻。
《歸》,180×180cm,布面丙烯,2024
《天堂》,160×140cm,布面丙烯,2024 未來 無論如何,藝術遠遠沒有終結,繪畫藝術也遠未面向死亡,翟春陽的“盜火計劃”既是對個人、社會和歷史的反思,也是對繪畫藝術的重塑,計劃從未改變! 注釋: 1,“三線”包含兩方面意思,一指三線城市,二指上世紀六十到八十年代基于工業、科技、國防和交通建設制定的“三線建設”戰備計劃而劃分的地理區域。 2,格林伯格《架上繪畫的危機》:它卻非常接近于裝飾——接近于那種可無限重復的墻紙圖案。 3,阿瑟·丹托《藝術終結后的藝術》。 4,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洞穴之喻”(Allegory of the Cave)描述對人類知識的基本想象。 藝術家簡介
翟春陽 藝術家,湖南省油畫學會理事。 1981年出生于湖南懷化,2006年畢業于西安美術學院油畫系司徒立具象表現主義工作室,現工作和生活于湖南長沙。 參展與獲獎經歷 2023 湖南省油畫學會十周年作品展,李自健美術館,長沙 2022 “重新提問”藝術展,庫藝術中心,北京 2020 “脈”中國當代繪畫展,亞洲美術館,日本福岡 “繪畫不死”作品展,庫藝術中心,北京 2015 湖南省第七屆油畫作品展,后湖國際美術館,長沙 2014 “當量”2014湖南省油畫學會年度作品展,力美術館,長沙 2009 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湖南展區優秀作品獎 2005 全國八大美術學院造型基礎大展,中國美術館,北京 |